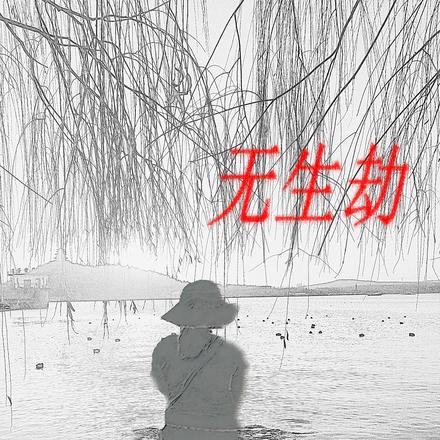杨庆来十七岁时,被生产队队长杨连玉安排去南排河修河坝。杨连玉对他说:“等修河回来,你就能挣大人工分,每天八分。”
当时,与杨庆来一起去修河坝的还有主任张万胜、社员白凤贵等人。他们背着行李、扛着铁锨来到泊镇火车站,没买票就上了火车。火车开到大满庄站,乘务员发现他们没有购票,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撵下了车。因等快车通过,杨庆来他们乘坐的这次列车要在大满庄站停靠四十分钟。于是,张万胜急忙去售票口补了票,然后他们拿着票重新上了车。半个小时后,火车到了冯家口车站,他们下了车,一路走着去了修河工地。公社带队领导、社长王波文亲自给他们安排了睡觉的窝棚和吃饭的食堂。第二天,他们加入到第六连队十排,大家推着插着红旗的小车赶赴工地,投入到紧张繁重的劳动中。修河的社员在食堂吃饭不限量,杨庆来得以天天吃饱。他正是长饭量也长身体的时候,一吃饱饭,就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那辆装土的木轮车最大,每次他都用力地驾起排满黄土的小车,似乎永无疲倦地穿梭在工地上。杨庆来干劲儿十足的样子,受到了社长王波文的好评。十六天的时间,王波文两次在大会上表扬了他。
修河工程还没完工,杨庆来就被村里调回来,到石桥和余庄联合成立的铸造厂上班。那年的12月20号,根治南排河工程阶段性完成,苏屯公社党委组织召开胜利竣工大会,会上,给早已到联合厂干活儿的杨庆来颁发了一枚劳动模范奖章。
这是1963年的事情。这一年,农业生产形势已有所好转。为此,国家倡导农村集体搞副业,以促使乡村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于是,公社的领导将石桥和余庄的村干部们叫到一起,让他们联合成立一个村级企业。各村从城市回来的职业工人,成为联合企业十分难得的人力和技术资源。
到工厂上班,是当时村里最好的工作,生产队不但一月给记三百工分,每月还能从厂子挣三块钱。跨进厂门后,杨庆来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那样神秘。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辈子也有机会进厂当工人。他觉得,这应该和城市工人没有多大区别。没有了下地干活儿时的风吹日晒,而是跟着师傅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车间里学技术;没有了春种秋收的辛劳,而是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看着那从高炉里淌出的红红的铁水,他与厂子所有工人一样兴奋,一样自豪。他认为,在这个火红的年代,在这个火红的时刻,已经开启了他向往多年的红红火火的人生。
杨庆来非常珍惜在厂里的工作和学习机会,更看重跟着师傅学混砂、学造型、学打芯儿、学刷浆刷粉、学熔炼浇注的每时每刻。他认为,工厂的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最拿手的技艺,如果不是国家精简城市职工,他是无缘给他们做徒弟的。他下决心要抓住这个机遇,认真地向各位师傅学习。古人讲,艺不压身。他认定,本事学一点儿是一点儿,学会了就是自己的,是自己一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深得师傅们的认可。哪位师傅也喜欢聪明伶俐的人,喜欢虚心好学的人,更喜欢勤劳能干的人。懒惰的人,不止手脚懒,脑子也懒;勤快的人,不仅身手勤谨,脑子也勤奋。师傅乐意教,徒弟乐意学,让杨庆来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铸造工序的各种手艺,为后来当领导、办企业夯实了技能基础。
杨庆来经常受到时任厂长的刘连茹师傅和外水刘汉山师傅的表扬。带过他的师傅说:“庆来脑子灵活,有些活儿一看就会,一点就透。”以致后来,那些教过杨庆来的师傅,遇到技术上的难题,都去找他商榷。甚至,厂子来了新铸件的图纸,师傅们都拿着让杨庆来去识去看。
工厂的老师傅们,都是很小就去城里当学徒工,大多数没有文化。他们不识字,自然就看不懂图纸。杨庆来虽然文化也不高,毕竟上了七年的学。而且,他对自己进入工厂很满足,对工厂的一切充满兴趣和乐趣。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一有时间就看书学习,写材料,做日记。渐渐地,杨庆来成为厂里唯一能看懂各种图纸的人。
杨庆来每天都早早地去联合厂上班儿。上班的路上,他顺带着卖些东西、收些废品。一般情况下,他赶到厂子时,工人们正在陆陆续续地进车间。这天,他还没进厂门,就远远地看到自己的师傅站在外面。师傅等他走近,便面无表情地对他说:“这一回,你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收破烂了!”
杨庆来心里一愣,急忙问:“怎么了?你说的是吗意思?”
师傅依然苦着脸,好像多余的话都不愿对杨庆来说一句。他扭头一指,冷漠地说:“你自己去看看吧。”
杨庆来快步走进厂里,看到几十个工人都在厂院儿里站着,你一句我一句地嚷成一团。他听了半天,最后才弄清楚,原来他工作两年多,用一腔心血、满脸汗水撑起的这个厂子干不下去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买卖好做,伙计难搭。这正是,两个人租船船漏,两个人养驴驴瘦。两个村联办的工厂,一开始那阵儿还好,后来盈利越来越大,村与村的矛盾就越来越多,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厂子只好关门大吉。杨庆来曾听师傅们议论过,说两个村也好,两个人也好,合伙办厂的都干不长,往往是赚钱也出意见,赔钱也出意见。闹好了,最后好分好散;闹不好,会撕破脸儿大打出手,成为一辈子的仇家。
厂子停产,受损失的虽然是两个村的经济,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些以厂为家的工人。越热爱厂子的人,受到的伤害就越大,杨庆来便是其中之一。尽管铸造厂的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却早已成了工人们的生活依托和精神依赖。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厂里干活儿的日子,突然离开工厂,顿时就觉得六神无主,心里空荡荡的,一双腿不知迈向哪里,一颗心再也无处安放。
杨庆来呆呆地在人们身后站了一段时间,最后听了师傅的话,到村里去收破烂了。他早晨来时走了南线的苏屯、南马庄村,这一次有了充足的时间,决定走北线的八里庄和肖杜李,然后经西庞回家。他不愿意到家太早,想在外面排遣沉淀一下自己烦懑的心绪,也想让家里人尽可能晚一点儿知道厂子解散的消息,晚一点儿知道他再也挣不到联合厂工钱的事。
天气闷热,他心里闷烦,两相交迫,是一种尤其难捱的煎熬。他盼着忽地刮起一阵风,吹走他的焦躁,剩下一地清凉;盼着忽地下起一场雨,将他心中所有的迷惘困惑和忧愁懊恼都打落在脚下。
到了肖杜李村,他感到口干舌燥,就跟着一个卖破烂的老太太回家,拿起她家灶台上的舀子,从缸里取了半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一时间,他竟然觉得身心轻松了许多。
快出村时,杨庆来闻到了那种小葱炝锅的味道。他喜欢这种味道,更喜欢用小葱炝锅后做出的热面汤。那用手擀的薄薄的面片儿在开水里滚几滚,快出锅时点上几滴香油,比山珍海味还好吃。
他抬头看看,见村子里有几户人家的烟囱里正冒着或浓或淡的炊烟。他不曾想,此时已经到了做午饭的时间。于是,他放弃了去西庞的打算,径直回了家。一进胡同,他又闻到了小葱炝锅的味道。他不由地想,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馋热面汤了?!
杨庆来越往家走,炝锅的味道越浓。进了家门,他才发现那香味儿已经充满整个庭院。他将从各村收来的废品放到院子的一角,快步走进屋里,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台前拉着风箱,锅里漂着葱花的水在慢悠悠地旋转着。
“俺从肖杜李就闻到炝锅的味道儿了!”杨庆来笑着说。
母亲抬头看了一眼杨庆来,说道:“你鼻子够长的!你怎么不说从北京就能闻到呢?!”
“谁说北京闻不到?”杨庆来煞有介事地说,“全国人民要是都做热面汤,他老人家一定闻得到。”
“你跟看见似的!”母亲讪笑着,说:“你还不快去洗手?看你那俩手脏的!”
杨庆来向母亲笑了笑,疑惑地问:“今儿是吗日子?怎么想起做好吃的来了?”
“听说厂子关了,怕你别扭得吃不下饭,想给你改善一下胃口。”母亲解释道,“厂子关了也就关了,大不了工厂的钱咱不挣啦,回来接着种地。”
“原来你都知道了?”杨庆来心里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慰藉的神情。这几年,他一直不愿将自己在外面的坏情绪带到家里来,从而让家人跟着受影响,跟着愁苦郁闷。他认为,一个大男人就要有担当,不管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家前也要擦干泪水,在亲人面前露出欢快的笑脸。
父亲从外面走进来,插言道:“厂子一关,最倒霉的是从城里下放回来的那些人!他们在车间搞铸造还行,去地里干活儿都是外行,有的罪受了!”
“有吗可受罪的?”母亲看着父亲辩驳道,“庄稼活儿能有多少技巧,哪能跟铸造手艺比?不说是个人就能干,也没三天的外行。在厂子干活儿好的,地里的活儿也一定能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