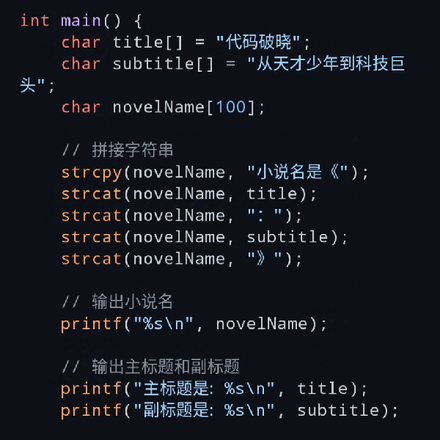整整一天都是在荒郊野外,又是白日里虽没下雪,风却断断续续的刮了一天,阮宁儿回了自己房间后叫人烧了热水,好好泡了一会原想发发汗的,中途觉得头昏脑胀便草草出了浴桶,简单吃了些点心,喝了姜汤就上床休息。
不曾想第二一早丫鬟过来送水见阮宁儿还未起床,挂起帐子之后才发现阮宁儿脸上有不正常的潮红,又伸手摸了摸她阮宁儿的额头烫的吓人,就着急跑出去喊人红姑。
红姑听后也是一惊,阮宁儿身子一直强健,这两年更是连小病小灾都没有,这次陡然生起高热来,怕是病的不轻,连忙着人去请惯常来的李大夫。
李大夫年逾五十,看着一丝不苟的模样,来了之后倒很是镇定,细细问了阮宁儿最近两日的情形,诊脉结束之后思忖良久才下笔开方,吹开递给了满目担忧之色的红姑。
许氏这清风院上下但凡哪个有头疼脑热都是请的这位李大夫,红姑也没有多想,就让一直在屋里候着的秦呈快去抓药回来,看阮宁儿这模样当真耽搁不得。如今阮宁儿是清风院的头牌,好些个达官贵人也是三不五时的豪掷千金请阮宁儿献艺,要是阮宁儿病的太久不能待客,会让人觉得是阮宁儿仗着几分名气找个生病的托词驳他们面子。
因着教坊司的规矩在,这些贵人对不会真对阮宁儿如何,但是让她吃些苦头还是很容易的。红姑自觉不是心狠的人,可这个时候一边盼着阮宁儿早点好,还不想耽搁生意,要不她也不好向教坊司交代。
红姑这般想也并非没有道理。
。。。
昨日贺家兄妹回到大将军并没有跟长辈说白天里发生的事情,虽然有波折,但是真正有损失的严格说起来只有贺煜。薛略也不会提,如果他说了反而会被薛尚书以荒废骑射为由责罚一顿。阮宁儿她是苦主之一,受惊昏厥大家都看在眼里。
作为大将军府不管如何要做做姿态,所以今天一早就来了两位管事带了厚礼分别送往薛尚书府与清风院,聊表歉意。
来清风院的贺家管事,开口便是想见阮宁儿当面将薄礼奉上,待红姑解释说宁儿姑娘自昨日回来就病了,刚刚喝过药正在休息,这位管事登时就撂了脸子,一脸倨傲的哼笑几声就转身走了,任红姑跟后边追出去也没停留半步。
。。。
因为之前许多准备都是提前安排下去的,秦呈最近都在配合阮宁儿搜集贺/宋两家的资料,与阮宁儿少见了几次,知道阮宁儿昨日是跟周宰出去的,他便没有安排其他人暗中跟着,对于昨日的情形并不清楚,哪知今日早起就听说阮宁儿高热不止,就借机进了阮宁儿住的小院子候着,一是想知道阮宁儿病情如何,另一个是想看能不能帮什么忙。
将李大夫开的方子揣进怀里,秦呈转道去了与西市挨着的光德坊,那里有商都最大最好的药铺杏坛药铺。
除了清风院的工钱,阮宁儿与秦呈他们一直有别的营生赚钱,要是否则许多事根本办不成,所以阮宁儿或者秦呈并不差钱。
原以为阮宁儿服了药病情能有起色,哪曾想连着喝了两天都没有效果,脸上却泛起了不正常的黑紫色,红姑与秦呈等人这才觉得事情大条了。
在叫李大夫来看时,李大夫自己嚷嚷着绝不是药方的问题,自己的方子都是用老了的,不可能出现问题,阮姑娘看着像是中毒了。需要精研毒方的大夫才能解,自己不擅长。
一听这话,红姑气的都想上去扇他耳光了,最后好在克制住了,可秦呈就没这么好说话,一把扭住李大夫的胳膊,问是怎么回事,你的方子要是没问题,我抓的药也是最好的,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李大夫吃痛大叫,依旧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他真不知道,秦呈推搡了下,把李大夫甩到了角落里跌在地上,嘴里直吸冷气。好在李大夫医德不错,自己爬起来慢慢踱到阮宁儿的病床前,仔细看过一遍,半晌才道,“阮姑娘中的毒似乎与昭成十六年……”
说完自己马上捂住嘴,使劲摇头。
昭成十六年的太子中毒案死的人太多,即便到现在偶尔有人提及也是闻之色变。
“不对,不是,只是看着像而已”,李大夫又言,“当务之急,快去萃菁堂请医毒大家百草先生。”
秦呈此时也冷静下来,闻言转身就出门了。哪知找到萃菁堂的时候被告知,百草先生应故人之约,早已离开商都,腊八之前才能回来。
伙计知道性命攸关给指了条路,“商都还有一位名声不显却极出色的医毒名士,就是不太好请。不过教坊司想来总能找到请托之人,或可一试。”
“是谁,在哪里?”秦呈忙问。
“东宫有位鸣鹤先生,精研医毒两道,常与我家先生切磋,对他很是钦佩。小哥或者能请人去请鸣鹤先生出手,贵姑娘应该无碍。”伙计接着说道。
秦呈听过,从萃菁堂出来边走边思索找谁去请身在东宫的鸣鹤先生,要是鬼医在商都的话也不用这般大费周章了,可是鬼医一直留在北地,此时来商都风险太高。
目前相熟或是能去东宫请动的人的,只有韩小王爷周宰,跟杨太师府的杨白公子,真要把握更大出入东宫方便的,是周小王爷无疑。想好请谁,秦呈沿着萃菁堂往东去后又左转直行良久才到了永兴坊外头。
韩王乃是昭成帝的同胞弟弟,兄弟二人差了年岁,昭成帝对这个弟弟很是疼爱,太后尚且在世,平日里赏赐不绝,就连韩王府也是一再扩建,如今几占半坊之地。
来到韩王府门前秦呈也没有直接上前,而是看着进出的人有没有面熟能给通传一二的。从九月十六以后,周宰常去清风院,连带着他的随从秦呈都能说上几句话。没多久,秦呈就等来了一位见过几面的周宰的侍从,忙从角落里追出来拦人,口称常四哥。
常四哥记性也好,看清来人相貌,就叫了出来,“秦小哥,怎么在这?可是你家姑娘有何事?我家小王爷进宫了几日一直没回来。”
秦呈有些傻眼,没想到是这个局面,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犹豫起来。
“我家姑娘那日与小王爷外出行猎,回来后就高热不止,请来的大夫开了方子一直不见好,今日看着不大对,却又说像是中毒了”,秦呈没办法,就继续说,“我去萃菁堂问过了,商都善解毒的百草先生不再城中,另一位或能解毒的先生在东宫,我想……”
常四哥脸色变得尤为精彩,心说,他家小王爷回来就提了几句,也没说有人中毒。可别真是去西郊山林碰到了什么奇毒,到时候他们小王爷脸色可不好看。
“秦小哥,我家小王爷在宫里这两天等闲回不来,我与你去宫门外的侍卫处等找人去通报一声,看小王爷如何决定。”常四哥道。
。。。
韩王府与皇宫相邻,两人拐向西侧,沿着东安大街走到韩王府与皇宫出入最便利的宫门承熙门外。除非宗庙祭祀或是大朝等,平日里韩王府进出皇宫都是从承熙门出入。
常四哥也没耽误,到承熙门当值的侍卫处的人说了一声自己乃是韩王府下人,有事需要找小王爷,请着人通报,说着递上了几粒金瓜子,这金瓜子还是临过来时秦呈给的。
那侍卫刚接过金瓜子,就看到远处有个头戴金冠,衣着锦裘的青年男子一脸寒霜的盯着自己,身上一僵,忙弯腰行礼,口呼“见过郡王。”
常四与秦呈见状也都弯腰行礼。
在商都的郡王有好几位,但是年岁与形容能对上的只有肃兴郡王周寒。周寒或是因为名字的缘故整日里都是一副面无表情,冷漠至极的模样,一张俊脸就有些不人耐看。
见肃兴郡王一直盯着自己,那侍卫小步走到面前周寒面前,低声道,“韩王府属人有急事要找小王爷,特来让小的通禀。”
周寒一言不发就盯着常四,常四随周宰四处应酬也见过肃兴郡王,但都是远远跟着,极少近前,见肃兴郡王盯着自己,声音有些瑟缩,“回郡王爷,是清风院的阮姑娘有急事求到我们小王爷,我这才来……”
一直老老实实弯腰立在旁边的秦呈头都没抬就能感觉到一道探究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虽不知道肃兴郡王因何知道自己是清风院下人,但是很肯定是周寒在看自己,遂快步近前,“见过郡王爷,小的乃是清风院下人,院里的阮姑娘日前去城外打猎,回来后高热昏迷,喝了两天才不见好,大夫才说像是中毒了。城中能解毒的百草先生不在,小的就想请小王爷帮忙请其他先生。”
秦呈在常四面前可以说阮宁儿与韩王府小王爷一起打猎后中毒的,但是在肃兴郡王还是这么说就有攀诬之嫌。
周寒略一思索,觉得哪里不对,又看向常四,常四一脸无奈,“是我家小王爷邀阮姑娘打猎的。”
“等着。”周寒听完,撂下一句,转身进了宫。
约莫半个时辰,周寒再回来的时候,旁边跟着一位穿鸭青色长衫的中年人。此人脸色红润,眼中莹润有光泽,宽袍大袖,走动间带着一股仙风道骨不惹凡尘的风采。天寒地冻的时节,仿若不知冷热,衣衫相对穿着锦裘的肃兴郡王要单薄许多,想来就是那位鸣鹤先生。
几人躬身行礼后,就见承熙门侧门走出,一位背着方盒穿着青衣的小吏,身后有位车夫左右控着一辆马车,右手拉着一匹体态修长,四肢健壮的骏马。
待到近前,周寒伸手拍了拍马背,脸上难得露出一丝笑意,随即招呼几人上车,便当先打马走了。
鹤鸣先生也不言语,撩起鸭青色长衫轻巧的进了车厢,那位青衣小吏紧随其后,也进了车厢。秦呈跟也跳上了车辕,跟车夫并排坐着,紧跟在周寒的后头,一起往清风院而去。常四没跟去,就想着留在宫门外万一小王爷出来可以说一声。常四私心觉得,虽不知道为何,这位阮姑娘如今在小王爷的心里还有几分重量。
。。。
看着肃兴郡王到了眼前,周身弥漫焦躁的红姑大吃一惊。好在跟在后边的秦呈快走了几步,低声向红姑解释了几句。也没多解释,只是路遇肃兴郡王,是郡王帮忙请来了这位精善医毒之道的鸣鹤先生。
打眼看去,肃兴郡王旁边跟着的那位先生,自有一份仙风道骨气韵,想必大有来头,也不多问,带着几人就去往阮宁儿的房间。
开门众人就闻到了房间中弥漫的一股松木香气,尤其是鸣鹤先生,更是在房间里来回打量,见到房间里没有摆放任何松木或盆景,不由挑挑眉。走近看清阮宁儿的苍白脸色,又从那位小吏手里接过方盒,取出银针,对着阮宁儿的耳垂刺了一针,见血后放在鼻尖嗅了嗅,随即有一脸恍然之感。
“确是中毒,不过毒性不大,最多让人燥热昏睡几日。只是这毒不常见,不必惊慌。”
鸣鹤先生如此说着,起身来到桌前取来纸笔开方子。
周寒见鸣鹤先生起身后,往前稍微探了探身子,只见阮宁儿的面容透出一股病态的苍白,依然如花般娇艳,整个人有几分颓废与绵软,却散发着一种与病态相悖的神秘与妖娆。
写完药方之后,鸣鹤先生就与肃兴郡王出了清风院,将那位青衣小吏留下,待阮宁儿服药后约莫半个时辰。一直守在旁边的丫鬟发觉阮宁儿眼球微动,似是要苏醒,少顷又兀自睡了过去。
小吏又来探查一遍,觉得已经无甚大碍,就施礼告辞。
小吏回到东宫,是在东宫所属的一间小药房里找到了鸣鹤先生。将鸣鹤先生与肃兴郡王离开之后的经过之后仔细说了就退下了。鸣鹤先生听完之后,低头思索了几分,便不再多言。
转身去往东宫的偏殿找太子殿下。
肃兴郡王能这么快从东宫请到人,要是没有太子点头,也不太可能。之前回到东宫的时候,鸣鹤先生没有见到太子殿下,此时过来,也是想回禀给阮姑娘解毒的经过。
。。。
太子周宗乃是昭成帝元后宋皇后嫡出,生于昭成二年,今年不过二十四岁,虽处盛年,可自昭成十六年中毒后,周宗原本英朗俊逸的面庞如今被已被残毒侵蚀下,只剩苍白与疲惫。他眉宇间虽是平静安详,可眼底弥漫的痛苦,只有他与身边亲近的人才知道。
鸣鹤先生进殿后先与端坐长案后的太子见礼,之后上前替太子诊脉,周宗无声的笑了,笑容有些讽刺与坦然。
鸣鹤先生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太子在承受着巨大的痛楚。冠服下有些瘦弱的身躯也是垂垂欲坠,连呼吸都显得异常沉重。
太子抽出手来,“老样子,还是苦熬着罢了”,不知道是病痛所致,还是在思考,太子顿了顿,“今日寒堂弟请先生去医治的那份阮姑娘如何了?”
“正好与殿下禀报此时,那位姑娘运气似极差。西郊山林中有一种名叫香雪兰的奇珍,只在冬季盛开,且数量稀少。虽以兰为名,却是一种乔木,常伴着松木而生,如果遇到点燃的琥珀松木会产生一种似有似无的松香。这种香气本身无毒,只是遇到寒檀引的话会让人陷入昏睡,起初几天高热不止,十日之内会自行解毒,就是人清醒后会有几日的无力感。”鸣鹤先生虽不知道为何太子殿下让自己随肃兴郡王去为阮宁儿解毒,可还是仔细回禀了今日看到的情形。
“鸣鹤先生是不是也觉得这中毒的方式耳熟的紧?罢了,无碍就好。”太子听鸣鹤先生说完更觉讽刺了。
吱呀,殿门被推开。
一位云鬓高环,头戴金钗,面如满月,眼如水银的高贵女子进来,手上端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一碗热气淼淼的汤药,香气氤氲。
见到这位女子,太子似乎才卸下所有的伪装,展颜一笑,笑容直达眼底。
“见过太子妃殿下”鸣鹤先生施礼。
“先生也在。”太子妃傅氏是天南滇王府的郡主,与太子周宗青梅竹马,到了年岁便成婚了。
太子见太子妃将托盘递过来,眼中闪过一抹无奈和宠溺,双手拿起药碗,一口喝下。
“如果肃兴郡王或是其他人再来请先生,还请先生尽力而为。”太子放下碗,对着鸣鹤先生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