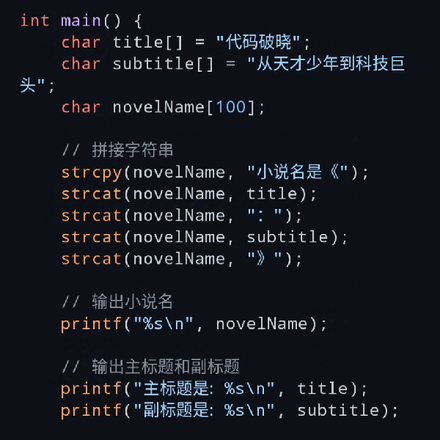夜色渐深,几位公子的兴致依然高涨,裹着斗篷来到扶菊小筑前欲对月畅饮。清风院作为帝都最大的消金窟之一,总也有些特色,直接在亭前点燃了篝火,让这些没去过边地的王孙公子们围坐在一起对着正中的半月吟诗作对,见此周宰兴起,让善音律的杨白踏歌,自己跑到场中起舞。
红姑生在北地长在北地,阖家女眷没入教坊司也在北地,能来商都经营这偌大的清风院,是红姑在教坊司那里争取的,也是阮宁儿一帮人在背后使力的结果。来了商都,红姑就把北地常见,商都不常有的玩乐之法带了过来,让本就以清倌人歌舞双绝的清风院又有了些不同。
看场中的开怀大笑的周宰就知道,这些不同,很对他们的脾胃。
。。。。。。
有乐声传来,一下子打乱了杨白的节拍,也扰乱了周宰肆意洒脱的舞蹈。
有一女子自几丈外的菊花丛中出现,一身素白衣裙,映着天上的月色与火光,时隐时现的脸庞有种妖异的美感,难以形容。
再次出现时,阮宁儿在月光起舞,身姿轻盈有力,有种北地的粗犷之美,仿佛一株在风中摇曳的曼陀罗花。与前次跳舞不同,现在的她,容颜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娇艳,很是魅惑。
阮宁儿的身姿优美,舞步轻盈,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长发在月光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随着她的舞姿飘扬;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光芒,宛如仙女下凡,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仿佛沉醉其中。
在月光下,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她的舞蹈仿佛是在诉说着她内心深处的愁绪,思念以及难言的破碎,让人心生怜惜。
阮宁儿借着月色借着每次转身,有几回刻意的往柳策看去,眼波流转,欲语还休。
因为分寸掌握的极好,周宰包括才思敏捷的杨白都没看出破绽,反而是柳策自己有几分不自在,阮宁儿要的就是这几分不自在。
一曲终了,阮宁儿没有多言,盈盈施礼后缓步退下,再没出现。徒留众人在场间愣怔。
。。。。。。
可能是阮宁儿的这支舞太有冲击了,让这些见惯或初见歌舞的王孙公子都是兴致缺缺,没多久就散了,各自家去。
只不过,或是步行,或是坐车乘轿的年轻人,翘起的嘴角就没下来过。
回到家,柳策家中,就有下人过来说,“老爷交代下来,等公子回家后去前院书房找老爷。”
柳策也没有迟疑,本也没有饮多少酒,身上酒气不重,没有换洗就去了前院书房见父亲。
柳问如今任朝中要职,对于今上与太子的身体情况要更了解些,但是谨慎期间,柳问从未透露过偏向任何一位皇子的意图。柳策的棋风也是与父亲柳问一脉相承下来的。
“父亲,我以为您已经休息了,想着明天再来拜见。”见到柳问,柳策躬身问安行李。
柳问放下手中的书卷,对柳策招招手,“读书有所得,还没来得及睡”,“今日赵世子庆生宴请如何?”
柳策知道父亲要问就将今天宴席事无巨细的都讲了一遍,只不过隐去了大半与阮宁儿相关的事。柳策关心的也不是阮宁儿,虽听出错漏,自觉无妨,也就没有深究。
捻须沉吟了一会,柳问看着柳策,“对今天参加宴请的这几位公子,我儿怎么看?”
柳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细细想过,半晌才道:“当今在世的勋爵以敏国公赵家、镇国公容家为首,镇国公府有镇国公、承恩公两位国公,地位超然,且镇国公府年轻一辈都镇守边塞,虽寻常难以见到,但是宫里有太后在,北方草原还有个汗王女婿,除非情况特殊,镇国公不会干涉朝局,否则商朝难安。”
“而杨家不管如何都是杨家,韩王也依旧会是韩王;二皇子燕王背后是能与镇国公府容家抗衡一二的贺家,五皇子郑王的身后是跟朝堂近半官员有千丝万缕干系的宋家。”
柳问侧耳听着,没有言语,示意柳策说下去。
“与镇国公不同,敏国公府现任的敏国公才智不显,不会有太多建树。老国公年迈睿智,精心教养赵世子自是希望敏国公府能再进现辉煌。就今天赵世子的言行看,极有可能是藏拙”柳策继续说着。
“户部尚书霍家与禁军左统领丁家的两位公子我极少见,今日他二人也不算活络,而且中间两人出去了一趟,想来是暂时不想卷进储位之争;大理寺卿卫家公子一整日都不曾说过几句话,仿佛置身事外一般,想来这也是卫家的态度。至于兵部侍郎钟家的青云公子,我隐隐觉得,他似乎很早就做出选择了,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子。”
听完柳策的话,柳问开口,“钟家确实早就做出选择了,只是那个选择如今成了最不可能的人。”
“皇三子吴王?”柳策心思电转。
柳问没有回答,只是轻轻颔首,脸上似乎有一丝惋惜,让柳策觉得奇怪,不过没问出来。
“钟家不会支持朝堂里任何一位皇子,霍家跟丁家太招人眼目,也容易引猜忌,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旗帜鲜明的支持哪一位;早些年间发生过一些事,卫家只能做诤臣,那卫小子这般做派,不足为奇。我儿可猜到敏国公的意图呢?”柳问又问道。
“孩儿只能猜到敏国公府似乎在等待什么契机。太子寿数难定,最终如何不好说,皇二子燕王,皇五子郑王敏国公府即便投诚也是锦上添花;皇三子吴王远在番地结局难料;其他成年皇子中谁是那个契机孩儿尚未想到。”
听到柳策的话,柳问也说到,“赵老国公乃是钓鱼的好手,不见鱼儿不会下饵的,可他背后的江南水师实在太诱人了,他能忍到现在,所图岂能小了”,顿了顿,柳问又说,“我儿可与那赵世子多走动走动,未必不能窥一豹见全身”。
此时柳问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狡黠与深沉的智慧,像往常对柳策的教导那样,不会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立场,只让柳策自己多思多看。
。。。。。。
此时,身在清风院的阮宁儿也在与曹嬷嬷说起柳问。
曹嬷嬷听到柳问的名字原本平静的神情瞬间变色,啐了一口,冷飕飕的骂道,“这个阴险小人,当初靠着张氏那个长袖善舞的贱人,倒是博得一份好名声,否则小姐怎么会与张氏这个贱人相交,我那可怜的小姐甚至还想过定娃娃亲。可柳策那个小坏蛋却攀诬你父亲,柳问那个蛇蝎心肠的竟然不顾念半点情分,将我们英家定罪,呜呜,我可怜的小姐啊”。
听着曹嬷嬷每次提起柳问夫妇,连骂人的话也都是一样,阮宁儿哭笑不得。
许是骂累人,曹嬷嬷端起桌上的茶猛喝了几口,“哼,你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正经人家有几个置那起子外室的,大了肚子收不了场了,才还敢领到小姐面前”,曹嬷嬷哭骂到这,一下子抱住阮宁儿,“我可怜的小姐,就留下你这一点苗裔,还受这般煎熬,英家亡就亡了,为什么还要我的心肝受苦,呜呜”
阮宁儿听着曹嬷嬷的话,才想起来自己原来姓英的,可真是讽刺。
轻轻拍着曹嬷嬷的身子,等到她睡着了,阮宁儿扶她躺好,才起身出了院子。
秋月半悬西陲,夜色凉如水。阮宁儿紧了紧衣衫,“柳问,柳策,你们父子手上的沾的血总该还了。”
是夜,柳策睡梦中有神女在自己近前轻歌曼舞,仔细看那神女的面容竟与阮姑娘有几分相似,柳策一下子惊醒,好似意识到什么,自己伸手进被子里摸了摸,随即脸上满是羞臊。